米夏的一个毛病是,不管开什么帖子,总想先说点干货……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许多人生命中都会拥有、然后失去的“那个人”。
一、看不见的朋友
有时,我们会不小心撞见,孩子独自一人在房间里,对着空气说话,为一个不存在的人微笑和哭泣。
有时,你问起刚满6岁的妹妹,“这朵小花是给谁的?”“是给我的朋友Tom的。”可你确信,你们的周围完全没有一个叫Tom的人……
这些“不存在的人”在孩子9岁后大多突然消失了。
在科学的理论介入之前,这些现象往往被和灵异、错乱联系在一起,那些看不见的“玩伴”被当做了鬼魂、恶魔和精神疾病。
二、假想同伴(imaginary companions)
早期,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会幻想出一个“同伴”来陪伴自己的小孩,往往是存在心理缺陷、不善沟通的,他们构建一个假想的“同伴”来满足自己的“超我”所不允许的行为、获取那些得不到的需要,以一种防御机制来缓解压力。换言之,假想同伴的存在,因为这个孩子交不到朋友。早期学者进一步认为,假想同伴会无条件地满足孩子的愿望。这些结论,使得人们对假想同伴和孩子的“自主性游戏”(自己跟自己玩)产生了恐惧。
好在,一些后来的研究颠覆了这些偏见:Manosevitz、Gleason等人通过几项研究发现,这种现象在儿童中普遍存在,非常正常,儿童可以同时拥有“真实的朋友”和“假想同伴”,而且儿童和“假想同伴”的互动十分丰富,并不是同伴任由孩子胡来,他们会交流、会磨合甚至吵架。
一些进一步的探索,甚至发现了不得了的结论:拥有“假想同伴”的孩子,更不害羞、善于交往的比例更大!简而言之,和“假想伙伴”的互动,让孩子预演了社会交往,把一些人际规范内化于心,举个例子:
安妮有一个“朋友”叫爱丽丝,爱丽丝的人设是:善良、活泼但是身体比较脆弱,安妮喜欢(在自己的幻想中)照顾爱丽丝,给她讲故事、喂药……爱丽丝满足了安妮被需要、显得强大的心理需求,也在这种幻想中减弱了安妮对生病和吃药的恐惧。后来,学校里,一个孩子在跑步时摔倒了,血流了一地,别的孩子都吓了一跳,只有安妮“熟练”地跑上去,扶起了那个孩子,其他人都夸安妮很勇敢、会照顾人。
而21世纪的一些新研究(是中国学者做的),发现“假想同伴”也有不同种类,有的和孩子是平等关系,有的是不平等关系(欺负孩子,或者被孩子欺负),平等关系的同伴下,孩子才会有显著的积极成长,否则会有负面作用。这个不难理解,一个坏朋友会带来坏结果,欺负人也会带来坏结果。
三、我与“她们”的故事
我也有过假想同伴,但比起科学解释,我想用一个更美好的方式来解释。
有一种生物叫赞纳“Zanna”,它们是古老而善良的种族,只有孩子才看得见它们,孩子们给予了Zanna们关注、爱护和真心,Zanna则会变成各种样子来陪伴孩子,回报他们。等到孩子们长大,变成了自信的大孩子,它们就会悄悄离开孩子的身边,默默祝福孩子,然后在夜里孤单地消散,变成清晨的露水。
我拥有过不止一个Zanna,无一例外都是女孩子。她们的来历丰富多彩,有的是林中仙女,被猎人射断了尾巴,逃到了我的居所;有的是古时的侍女,温柔、人美心善;也有的是坏透了的恶魔,被我打败之后就不得不留在身边……她们的共性是,被我支配,同时被我爱护。我曾说我的属性是与生俱来的,没错,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就在脑子里养了一堆ṡṻḃ。但我认为我与她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因为在支配她们时,是她们在关爱我,在爱护她们时,是我在关爱她们。对她们,小时候的我有着奇怪的眷恋,是一种不像爱情,但绝不是朋友的关系,长大了我才明白。
可惜,我长大了,她们也不辞而别,也许也在月光下变成露水消失了吧。唉,真对不起,你们在的时候,我应该留下一些画、一些日记,现在你们什么痕迹都没有了。
接下来是问答环节:
隐藏内容需要登录才可以看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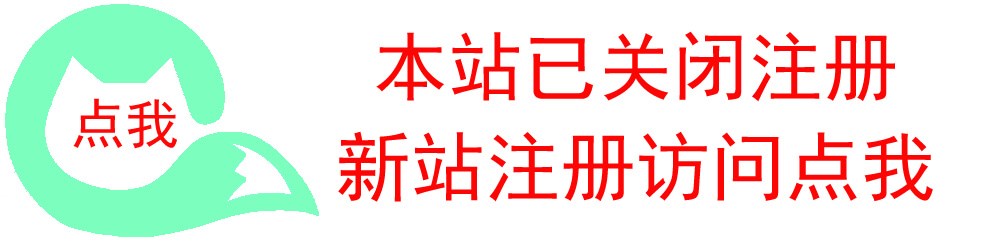

我觉得早先时候出现的不完整的意向反而是我刻意创造出来的,一直到现在为止很多人是活在我的意向里面的。在我个人的意识当中不是偶然出现,而是我自己去一点一点完善这些形象和细节,包括我们的相处,包括我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些人会在我身边。我们如何交流,交流的内容是什么。早些时候我认为是基于社交恐惧和社交障碍产生的自我排遣,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我发现这种自我排遣变得越来越多。反而更像是我刻意在制造他们一样,甚至有些“人格”已经到了近乎于我的不同人格的程度。
我写小说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安放这些自我创造出来的朋友,我觉得这种自我意识中产生的无形形象是不是更大程度上是在人的自我排解所构建的弭补型人格呢?
每次都被丰富的知识和世界观所倾倒,您太厉害了(狼嚎
我可以画您的同人图吗!
头脑特工里边那个棉花糖小象就是比较典型的,幻想玩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