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老式的小说装腔作势,矫揉造作,几乎到了滑稽可笑的程度,但当初读到它们的人,并不觉得那样。社会上和感情上的这种虚伪风气,今天仍大量存在。只要再放手加上一些附庸风雅的成分,你就可以大致领略到你所订阅的报纸书评栏的调子和俱乐部里读书小组一本正经、愚昧自满的气氛了。
畅销书就是他们这种人制造出来的。所谓畅销书,其实靠的是宣传推广工作,其基础是一种间接的附庸风雅的心理,有批评界的老朋友打上的印记做质保,有某些极有势力的幕后集团的精心爱护、不断浇水。这些集团的本业是推销书籍,但是却希望给你一种他们在推广文化的印象。你只要书款稍许迟付了一些,就可以明白他们标榜的理想主义到底是什么了。
雷蒙德钱德勒的句子:
半个世纪以前的很多文字放到现在的中国依然适用,经典就是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过时。另一个尼采与其说是对我有影响,更像是精神兴奋剂一类的存在,不太贴合现实,关于翻译的信达雅问题,尼采的中文译本倒是读起来依旧霸气侧漏,足够经典的文学就算半吊子翻译依然可以表达出原著的锐气,比如雷蒙德钱德勒的最后一本书《重播》,下面这个老版的译本有着粗犷的市井气质,倒也很贴合原作的冷硬派侦探气质,新版上海译文出版社这个太文雅了,魅力大减。
老版:
一阵刺耳、带着命令语气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楚,原因之一:我还没睡醒;原因之二:我把话筒拿反了。调正后,我对话筒嘟囔了两声。
“你听见没?我叫克莱德·乌姆内,我是律师。”
“叫克莱德·乌姆内的律师满街都是。”
“你就是马洛,是不是?”
“大概是吧。”我看看表,清晨六点半,这种时间我多半还头脑不清。
“别跟我放肆,年轻人。”
“很抱歉,乌姆内先生。我可不是什么年轻人,我有点年纪了,嗜咖啡如命。您需要我这种人为您效劳吗?”
“我要你八点钟去等SC列车,在那批旅客中会有一个女孩,我要你找到她然后跟踪她,查到她下榻的饭店,回来向我报告。清楚吗?”
“不清楚。”
“你是什么意思?”他生气地问道。
“光凭这些信息,我无法确定这个案子可以接。”
“你搞清楚我是克莱德·乌——”
“够了!”我打断他,“别把我弄得歇斯底里,你再把情况说明一下,也许你真正需要的是调查员,我一向自知不是干FBI探员的料。”
新版:
电话中的嗓音似乎既刺耳又专横,但我没听清它在说什么——部分原因是我依然半睡半醒,还有部分原因是我把话筒拿反了。我拙手笨脚地转过话筒,咕哝了一声。
“你听见了吗?我说了我是克莱德·安姆尼,那位律师。”
“克莱德·安姆尼,那位律师。我以为叫这名字的律师有好几个。”
“你就是马洛,对不对?”
“对。我猜也是。”我瞅了瞅腕表。凌晨六点半,不是我状态最好的时辰。
“少跟我放肆,年轻人。”
“抱歉,安姆尼先生。但我可不是什么年轻人。我老了,人很累,而 且一点咖啡都还没喝。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先生?”
“我要你八点钟去接‘超级酋长’号,在乘客中认出一个姑娘,然后跟踪她,直到她在什么地方登记入住为止,然后你要立即向我汇报。清楚了吗?”
“不行。”
“为啥不行?”他厉声问。
“我掌握的信息不够,没法确定我可以接这案子。”
“我可是克莱德·安姆——”
“少来这套,”我打断了他的话,“没准我要犯歇斯底里了。你把基本情况告诉我就成。也许另找一个侦探对你更合适。我向来不是干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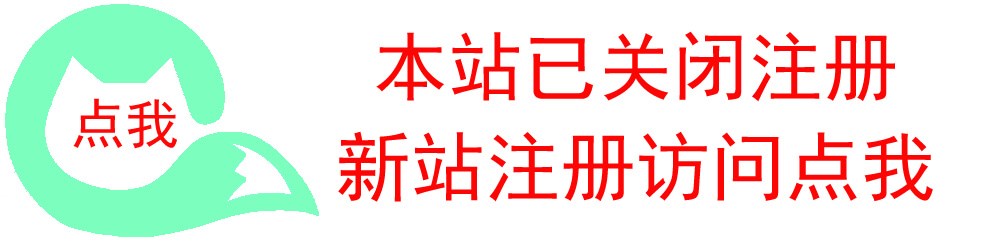





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
它的根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底。
很早就看到过,一直不理解,现在终于明白了。